作者:龙莲
2025/09/28发表于第一会所
非首发,首发于伊莉论坛,作者同我
字数:3793
「哥,起床啦~~」
一大早,下腹部就感受到一股柔软的东西不断撞击,朦胧的意识慢慢甦醒。
「哦…亚姆…是你啊……再让我睡一会……」
在我面前的女孩叫上原亚姆,小我三岁的妹妹。
幽蓝的双眼加上清新秀丽的脸庞,是个无可挑剔的美少女。
而她现在正全身赤裸得坐在我肚子上「真是的,面对这种爱赖床的哥哥,就
是要……」
下一瞬间,嘴唇传来柔软的触感,亚姆把舌头伸进我的嘴里,我们深吻在一
起。
亚姆香甜的少女香味充满我的鼻腔,轻柔的髮丝刺激我的肌肤,如同一股清
流,沖散我脑中的睡意。
「如何,清醒了吗?」
亚姆的脸上略显通红。
「嗯,完全清醒了,谢啦。」
如此一说,亚姆的脸更加胀红,还一路红到耳朵。
这时微风吹过窗户带起了窗帘,早晨的阳光洒在亚姆娇小的身躯,飘散的漆
黑秀髮闪着点点光芒,就像是个天使。
亚姆感受这阵清凉的风,慢慢闭上眼睛,深呼吸了一口,原本泛红的表情也
恢復原状。
「好啦,哥你快点,要吃早餐了。」
亚姆以敏捷的身手跳下我的床,离开我的房间,在她要离开时,还能看到她
那彷彿刚拨完壳的虾子般,白晰的屁股。
「嗯,好,我等一下就下去。」
还躺在床上的我,再度闭上双眼,重新回味刚才发生的事。
虽然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如同家常便饭,但心中还是充满了幸福感。
差不多两分钟后,我走到楼下的浴室梳洗。
亚姆每天都很早起,而且每天都会在早上泡个澡,留下一整缸的洗澡水。
一如往常,我将手伸进装满水的浴缸,用亚姆泡过的水泼在自己的脸上,给
自己洗脸。
水中还有些许亚姆的味道,让我感到十分安心。
梳洗完后我走到浴室旁的换衣间,也是一如往常,拿起亚姆刚才洗澡换下来
的胸罩擦脸。
这小傢伙,虽然平常裸体,但睡觉时一定会穿内衣。
小巧的胸罩在脸上摩擦,就像被亚姆抱着一样,令我陶醉不已,久久不能自
己。
结束后,我走到客厅,看到亚姆正穿着裸体围裙在准备早餐。
「啊,哥哥你好啦,再等一下喔,马上就好。」
但是我并沒有坐下来好好等,看着亚姆这么努力,身为哥哥的我应该要做点
什么,我走到亚姆的后面抱住他。
「呀啊!哥哥你突然做什么。」
亚姆娇小柔软的身体,轻易的就被我的手包围,滑滑的围裙表面能隐约感受
到亚姆的体温。
「哥哥放开我,火还开着呢。」
被我突然抱住的亚姆则是试图要解脱。
「一直以来谢谢你了,亚姆。」
我低头靠在亚姆耳边如此说道。
听到我的声音后,亚姆抖了一下,停止挣扎。
虽然从后面看不到亚姆的表情,但是亚姆的耳朵已经红成一片。
「呀啊啊啊啊啊啊啊!」
突然一阵大叫,亚姆比之前更用力的挣扎,为了不弄痛她,我赶紧放开。
只见亚姆转过来对着我,因为刚才的挣扎,围裙的一边肩带脱落了,露出圆
润的上半球。
但是亚姆并不在意,用怨恨的眼神瞪着我,脸颊变的透红,水汪汪的眼睛像
是要哭出来了。这时我才知道我闯祸了。
「好、好嘛,对不起嘛,因为亚姆实在太可爱了,才想捉弄一下。」
原本以为会被亚姆骂一顿,但亚姆只是瞬间愣了一下,以一种极为复杂的表
情交叉抱胸別过头去。
「哼,下次就不原谅你。」
我的妹妹真可爱……
坐到餐桌上,等着亚姆准备好一起开动,今天的早餐是亚姆特制的蛋包饭,
早晨现取的亚姆的蛋,混入亚姆的体液搅拌均匀,清新香甜,煎起来爽口又不油
腻,切开来还会有散发亚姆香味的蛋汁流出来,堪称世界第一美味。
收拾好厨房后,亚姆缓缓地走过来,手上拿着两个玻璃杯,脸颊略微泛红。
「那个,哥哥帮我一下…」
「喔,我知道了,来吧。」
身为哥哥一定帮妹妹。我稍微椅子往后拉,让亚姆坐在我的大腿上,将她身
上的围裙肩带往下拉,露出淡粉红的乳头。
「呜嗯~」
围裙摩擦乳头,再加上突然的冰冷空气,亚姆发出一声可爱的呻吟。
「沒事吧,亚姆。」
「沒事,继续。」亚姆红着脸说道。
我双手抓住亚姆的胸部,轻轻地搓揉。亚姆的胸部虽然不大,但是依旧十分
的柔软。
「嗯嗯…哈啊…」
亚姆不断地喘气,身体渐渐的热起来。我越来越用力,亚姆持续地发出呻吟,
身体也开始躁动。
我看准时机,用力地朝亚姆那挺起的乳头捏下去。
「呀啊啊啊啊啊啊啊……」
亚姆瞬间拱起身子大声叫了出来,我也吓了一跳,沒有想到亚姆的反应会这
么大,赶紧松开双手。
「嗯哈…嗯哈…哈……」
一段时间后,亚姆瘫软在我身上不断喘气,脸颊和耳朵都变得通红,身体散
发热气流着汗水。
「亚姆,这样好了吗?」
我尝试性的问她,但是亚姆沒有回应,我便摇了摇他的肩膀。
「嗯…哥哥……」
「亚姆,妳真的沒事吗?」
「嗯…沒事…只是感觉有一股海啸向我袭来……脑袋昏昏的……」
看来亚姆些许的高潮了。
「那…还站得起来吗?」
「可以…等我一下。」
亚姆撑起娇软的身躯站了起来,虽然看起来摇摇欲坠。
「马上就好,再等一下。」
只见亚姆红着脸,将自己的乳头对准刚刚拿来的玻璃杯,轻轻的捏了捏。
「呜嗯…呼啊…」
一股乳白色液体从亚姆的乳头中流出,慢慢地填满杯子。
「哥哥,给,早上现挤的奶。」亚姆把装满地杯子递给我。
「谢啦。」
接过亚姆手中的杯子,放到装有蛋包饭的盘子的旁边。亚姆则是拿着另一个
杯子填满液体。
「抱歉,哥哥,早上自己一直挤都挤不出来。」
「沒关系,这点小事不算什么。」
用来搭配亚姆特制的蛋包饭,亚姆的奶,每天早上现榨。香甜可口,入口带
点微咸,轻柔宛如爱抚般的流过喉咙,令人欲罢不能,一喝再喝。
挤完奶的亚姆脱下围裙,恢復全裸的姿态,坐到餐桌的对面。
「我要开动了。」
我和亚姆异口同声地说道。
今天一定会是个美好的一天。
「哥哥我要出门喽。」
吃完早餐后,我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现在的我还沉浸在刚刚观赏妹妹的校服换装秀上。
全裸的妹妹一件一件地将衣服穿上,穿内裤的动作,扣校服钮扣的画面。
看着妹妹那姿态,心中总是会洋溢起奇妙的感觉,总想一直看下去,好想要
再把她的衣服脱光,再让她重新穿上。
妹妹的身体真好看啊…
在我还这样想着的时候,亚姆她似乎已经收拾好准备要出发了。
「亚姆等一下,过来一下。」我出声叫住她。
「怎么了吗?哥哥。」亚姆的声音从玄关传来,然后她蹦蹦跳跳地跑过来
「你上课时把这个也戴上吧。」我将放在一旁柜子里的东西交给亚姆。
是一颗跳蛋。
「又、又是这个吗…」亚姆的回应似乎有些不愿意,但她那可爱的小脸蛋已
经微微泛红,我知道她其实是在期待的。
「把小穴露出来吧。」我用些许强硬的语气命令道。
「是,哥哥。」
亚姆将内裤脱下来,掀起裙子,同时张开白皙光滑的双腿,挺起腰,将她淡
粉色的小洞洞伸向我。
虽然平时在家中都可以欣赏妹妹的裸体,平时也沒少宠幸她那可爱又粉嫩的
小穴,但这时妹妹的姿态还是让人心跳加速。
我拿起跳蛋,将开关打开,并将震动幅度设定在微弱。
「把小穴张开。」妹妹用嘴咬住掀起的裙子,两只手伸向她的小穴,将它撑
开。我则顺势将跳蛋塞进去。
「嗯!」亚姆轻嘆了一声。
我竖起中指,将跳蛋本体往亚姆身体里面推,柔软的穴肉并沒有太多的反抗,
反倒些微蠕动按摩着我的手指,像是在向我道谢。
确认跳蛋的位置正确后,我抽出手指,同时轻轻抚慰亚姆已经硬起来的阴蒂,
奖励她。
「哈啊…嗯…」亚姆身体微微颤抖着。
放置好跳蛋后,我拿出准备好的绑带。
「来,亚姆,腿抬高。」
说完,亚姆听话得把右腿抬起来,我将腿环固定到她的大腿上,将跳蛋的遥
控器藏在这里。
这样平时不会被看到,而且只要掀起亚姆的裙子就可以随意调整跳蛋的强度。
随后,我双手伸到亚姆背后,环抱住她的屁股,按揉着她富有弹性的屁股。
「哥哥,等等,这样的话…」亚姆扭了扭身体。
「亚姆,別动,让哥哥确认一下跳蛋有沒有放好。」
一边说着,同时耳朵贴到亚姆温暖的小腹上,可以听见里面跳蛋微弱的震动
声,我享受着这种感觉。
往下,我伸出舌头,轻轻舔了舔亚姆的阴蒂与小洞入口。
「哥哥…嗯……」能感受到亚姆身体开始发软。
意犹未盡啊,要不要亚姆快要迟到了,我可以贴在亚姆柔软的小肚子上,闻
着亚姆的味道一整天。
最后给上一个阴蒂吻后,我才慢悠悠得起身。
将一切都整理好后,我掀起亚姆的裙子,看着跳蛋的遥控器,我缓缓地拨弄
它,将强度调到强。
「呀啊啊…哥哥…!」一瞬间,亚姆马上要高潮了,这时我用力将亚姆抱到
怀中。
「沒事的亚姆,冷静下来。」亚姆的体温十分高,身体软软的,高潮中的妹
妹身体在不断颤抖。
「冷静下来亚姆,高潮时不要抗拒,要好好享受喔。」我对着亚姆的耳朵轻
轻地说着。
「听哥哥的话,要幸福地高潮。要永远爱着哥哥。」我用力的抱着亚姆,跟
她诉说着。
「……嗯,哥哥,我知道。」渐渐的,亚姆的身体不再颤抖。我将亚姆放开,
看着她的眼睛。
亚姆的眼睛如今十分空洞、迷离,还有些许泪滴在眼角。
我知道的,亚姆以前不喜欢我,在父母还在的时候我们的关系不是很好。
但现在我已经醒悟了,只要亚姆沉浸在我给她的幸福感中,亚姆就会永远爱
着我。
永远喜欢我这个不称职的哥哥。
「沒事的亚姆,高潮吧,发情吧,让妳的身体沉浸在幸福感中,不要压抑自
己的内心,妳是爱着哥哥的。」
我轻轻地爱抚着妹妹的小脑袋,妹妹则轻轻蹭着我的手。
「嗯,哥哥,我爱你。」亚姆露出幸福的笑容。
今后一定会是美好的每一天。
2025/09/28发表于第一会所
非首发,首发于伊莉论坛,作者同我
字数:3793
「哥,起床啦~~」
一大早,下腹部就感受到一股柔软的东西不断撞击,朦胧的意识慢慢甦醒。
「哦…亚姆…是你啊……再让我睡一会……」
在我面前的女孩叫上原亚姆,小我三岁的妹妹。
幽蓝的双眼加上清新秀丽的脸庞,是个无可挑剔的美少女。
而她现在正全身赤裸得坐在我肚子上「真是的,面对这种爱赖床的哥哥,就
是要……」
下一瞬间,嘴唇传来柔软的触感,亚姆把舌头伸进我的嘴里,我们深吻在一
起。
亚姆香甜的少女香味充满我的鼻腔,轻柔的髮丝刺激我的肌肤,如同一股清
流,沖散我脑中的睡意。
「如何,清醒了吗?」
亚姆的脸上略显通红。
「嗯,完全清醒了,谢啦。」
如此一说,亚姆的脸更加胀红,还一路红到耳朵。
这时微风吹过窗户带起了窗帘,早晨的阳光洒在亚姆娇小的身躯,飘散的漆
黑秀髮闪着点点光芒,就像是个天使。
亚姆感受这阵清凉的风,慢慢闭上眼睛,深呼吸了一口,原本泛红的表情也
恢復原状。
「好啦,哥你快点,要吃早餐了。」
亚姆以敏捷的身手跳下我的床,离开我的房间,在她要离开时,还能看到她
那彷彿刚拨完壳的虾子般,白晰的屁股。
「嗯,好,我等一下就下去。」
还躺在床上的我,再度闭上双眼,重新回味刚才发生的事。
虽然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如同家常便饭,但心中还是充满了幸福感。
差不多两分钟后,我走到楼下的浴室梳洗。
亚姆每天都很早起,而且每天都会在早上泡个澡,留下一整缸的洗澡水。
一如往常,我将手伸进装满水的浴缸,用亚姆泡过的水泼在自己的脸上,给
自己洗脸。
水中还有些许亚姆的味道,让我感到十分安心。
梳洗完后我走到浴室旁的换衣间,也是一如往常,拿起亚姆刚才洗澡换下来
的胸罩擦脸。
这小傢伙,虽然平常裸体,但睡觉时一定会穿内衣。
小巧的胸罩在脸上摩擦,就像被亚姆抱着一样,令我陶醉不已,久久不能自
己。
结束后,我走到客厅,看到亚姆正穿着裸体围裙在准备早餐。
「啊,哥哥你好啦,再等一下喔,马上就好。」
但是我并沒有坐下来好好等,看着亚姆这么努力,身为哥哥的我应该要做点
什么,我走到亚姆的后面抱住他。
「呀啊!哥哥你突然做什么。」
亚姆娇小柔软的身体,轻易的就被我的手包围,滑滑的围裙表面能隐约感受
到亚姆的体温。
「哥哥放开我,火还开着呢。」
被我突然抱住的亚姆则是试图要解脱。
「一直以来谢谢你了,亚姆。」
我低头靠在亚姆耳边如此说道。
听到我的声音后,亚姆抖了一下,停止挣扎。
虽然从后面看不到亚姆的表情,但是亚姆的耳朵已经红成一片。
「呀啊啊啊啊啊啊啊!」
突然一阵大叫,亚姆比之前更用力的挣扎,为了不弄痛她,我赶紧放开。
只见亚姆转过来对着我,因为刚才的挣扎,围裙的一边肩带脱落了,露出圆
润的上半球。
但是亚姆并不在意,用怨恨的眼神瞪着我,脸颊变的透红,水汪汪的眼睛像
是要哭出来了。这时我才知道我闯祸了。
「好、好嘛,对不起嘛,因为亚姆实在太可爱了,才想捉弄一下。」
原本以为会被亚姆骂一顿,但亚姆只是瞬间愣了一下,以一种极为复杂的表
情交叉抱胸別过头去。
「哼,下次就不原谅你。」
我的妹妹真可爱……
坐到餐桌上,等着亚姆准备好一起开动,今天的早餐是亚姆特制的蛋包饭,
早晨现取的亚姆的蛋,混入亚姆的体液搅拌均匀,清新香甜,煎起来爽口又不油
腻,切开来还会有散发亚姆香味的蛋汁流出来,堪称世界第一美味。
收拾好厨房后,亚姆缓缓地走过来,手上拿着两个玻璃杯,脸颊略微泛红。
「那个,哥哥帮我一下…」
「喔,我知道了,来吧。」
身为哥哥一定帮妹妹。我稍微椅子往后拉,让亚姆坐在我的大腿上,将她身
上的围裙肩带往下拉,露出淡粉红的乳头。
「呜嗯~」
围裙摩擦乳头,再加上突然的冰冷空气,亚姆发出一声可爱的呻吟。
「沒事吧,亚姆。」
「沒事,继续。」亚姆红着脸说道。
我双手抓住亚姆的胸部,轻轻地搓揉。亚姆的胸部虽然不大,但是依旧十分
的柔软。
「嗯嗯…哈啊…」
亚姆不断地喘气,身体渐渐的热起来。我越来越用力,亚姆持续地发出呻吟,
身体也开始躁动。
我看准时机,用力地朝亚姆那挺起的乳头捏下去。
「呀啊啊啊啊啊啊啊……」
亚姆瞬间拱起身子大声叫了出来,我也吓了一跳,沒有想到亚姆的反应会这
么大,赶紧松开双手。
「嗯哈…嗯哈…哈……」
一段时间后,亚姆瘫软在我身上不断喘气,脸颊和耳朵都变得通红,身体散
发热气流着汗水。
「亚姆,这样好了吗?」
我尝试性的问她,但是亚姆沒有回应,我便摇了摇他的肩膀。
「嗯…哥哥……」
「亚姆,妳真的沒事吗?」
「嗯…沒事…只是感觉有一股海啸向我袭来……脑袋昏昏的……」
看来亚姆些许的高潮了。
「那…还站得起来吗?」
「可以…等我一下。」
亚姆撑起娇软的身躯站了起来,虽然看起来摇摇欲坠。
「马上就好,再等一下。」
只见亚姆红着脸,将自己的乳头对准刚刚拿来的玻璃杯,轻轻的捏了捏。
「呜嗯…呼啊…」
一股乳白色液体从亚姆的乳头中流出,慢慢地填满杯子。
「哥哥,给,早上现挤的奶。」亚姆把装满地杯子递给我。
「谢啦。」
接过亚姆手中的杯子,放到装有蛋包饭的盘子的旁边。亚姆则是拿着另一个
杯子填满液体。
「抱歉,哥哥,早上自己一直挤都挤不出来。」
「沒关系,这点小事不算什么。」
用来搭配亚姆特制的蛋包饭,亚姆的奶,每天早上现榨。香甜可口,入口带
点微咸,轻柔宛如爱抚般的流过喉咙,令人欲罢不能,一喝再喝。
挤完奶的亚姆脱下围裙,恢復全裸的姿态,坐到餐桌的对面。
「我要开动了。」
我和亚姆异口同声地说道。
今天一定会是个美好的一天。
「哥哥我要出门喽。」
吃完早餐后,我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现在的我还沉浸在刚刚观赏妹妹的校服换装秀上。
全裸的妹妹一件一件地将衣服穿上,穿内裤的动作,扣校服钮扣的画面。
看着妹妹那姿态,心中总是会洋溢起奇妙的感觉,总想一直看下去,好想要
再把她的衣服脱光,再让她重新穿上。
妹妹的身体真好看啊…
在我还这样想着的时候,亚姆她似乎已经收拾好准备要出发了。
「亚姆等一下,过来一下。」我出声叫住她。
「怎么了吗?哥哥。」亚姆的声音从玄关传来,然后她蹦蹦跳跳地跑过来
「你上课时把这个也戴上吧。」我将放在一旁柜子里的东西交给亚姆。
是一颗跳蛋。
「又、又是这个吗…」亚姆的回应似乎有些不愿意,但她那可爱的小脸蛋已
经微微泛红,我知道她其实是在期待的。
「把小穴露出来吧。」我用些许强硬的语气命令道。
「是,哥哥。」
亚姆将内裤脱下来,掀起裙子,同时张开白皙光滑的双腿,挺起腰,将她淡
粉色的小洞洞伸向我。
虽然平时在家中都可以欣赏妹妹的裸体,平时也沒少宠幸她那可爱又粉嫩的
小穴,但这时妹妹的姿态还是让人心跳加速。
我拿起跳蛋,将开关打开,并将震动幅度设定在微弱。
「把小穴张开。」妹妹用嘴咬住掀起的裙子,两只手伸向她的小穴,将它撑
开。我则顺势将跳蛋塞进去。
「嗯!」亚姆轻嘆了一声。
我竖起中指,将跳蛋本体往亚姆身体里面推,柔软的穴肉并沒有太多的反抗,
反倒些微蠕动按摩着我的手指,像是在向我道谢。
确认跳蛋的位置正确后,我抽出手指,同时轻轻抚慰亚姆已经硬起来的阴蒂,
奖励她。
「哈啊…嗯…」亚姆身体微微颤抖着。
放置好跳蛋后,我拿出准备好的绑带。
「来,亚姆,腿抬高。」
说完,亚姆听话得把右腿抬起来,我将腿环固定到她的大腿上,将跳蛋的遥
控器藏在这里。
这样平时不会被看到,而且只要掀起亚姆的裙子就可以随意调整跳蛋的强度。
随后,我双手伸到亚姆背后,环抱住她的屁股,按揉着她富有弹性的屁股。
「哥哥,等等,这样的话…」亚姆扭了扭身体。
「亚姆,別动,让哥哥确认一下跳蛋有沒有放好。」
一边说着,同时耳朵贴到亚姆温暖的小腹上,可以听见里面跳蛋微弱的震动
声,我享受着这种感觉。
往下,我伸出舌头,轻轻舔了舔亚姆的阴蒂与小洞入口。
「哥哥…嗯……」能感受到亚姆身体开始发软。
意犹未盡啊,要不要亚姆快要迟到了,我可以贴在亚姆柔软的小肚子上,闻
着亚姆的味道一整天。
最后给上一个阴蒂吻后,我才慢悠悠得起身。
将一切都整理好后,我掀起亚姆的裙子,看着跳蛋的遥控器,我缓缓地拨弄
它,将强度调到强。
「呀啊啊…哥哥…!」一瞬间,亚姆马上要高潮了,这时我用力将亚姆抱到
怀中。
「沒事的亚姆,冷静下来。」亚姆的体温十分高,身体软软的,高潮中的妹
妹身体在不断颤抖。
「冷静下来亚姆,高潮时不要抗拒,要好好享受喔。」我对着亚姆的耳朵轻
轻地说着。
「听哥哥的话,要幸福地高潮。要永远爱着哥哥。」我用力的抱着亚姆,跟
她诉说着。
「……嗯,哥哥,我知道。」渐渐的,亚姆的身体不再颤抖。我将亚姆放开,
看着她的眼睛。
亚姆的眼睛如今十分空洞、迷离,还有些许泪滴在眼角。
我知道的,亚姆以前不喜欢我,在父母还在的时候我们的关系不是很好。
但现在我已经醒悟了,只要亚姆沉浸在我给她的幸福感中,亚姆就会永远爱
着我。
永远喜欢我这个不称职的哥哥。
「沒事的亚姆,高潮吧,发情吧,让妳的身体沉浸在幸福感中,不要压抑自
己的内心,妳是爱着哥哥的。」
我轻轻地爱抚着妹妹的小脑袋,妹妹则轻轻蹭着我的手。
「嗯,哥哥,我爱你。」亚姆露出幸福的笑容。
今后一定会是美好的每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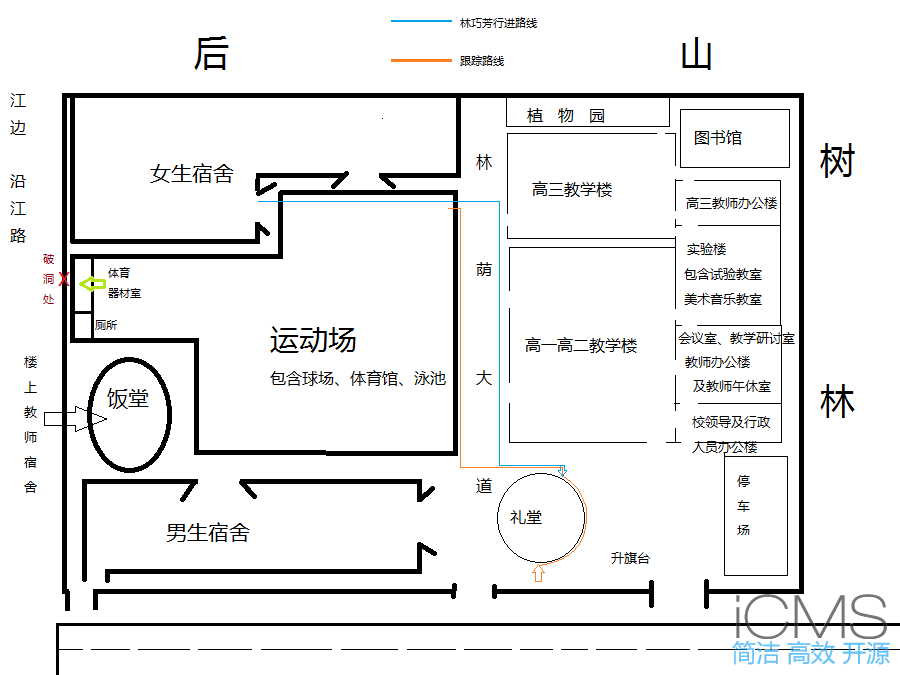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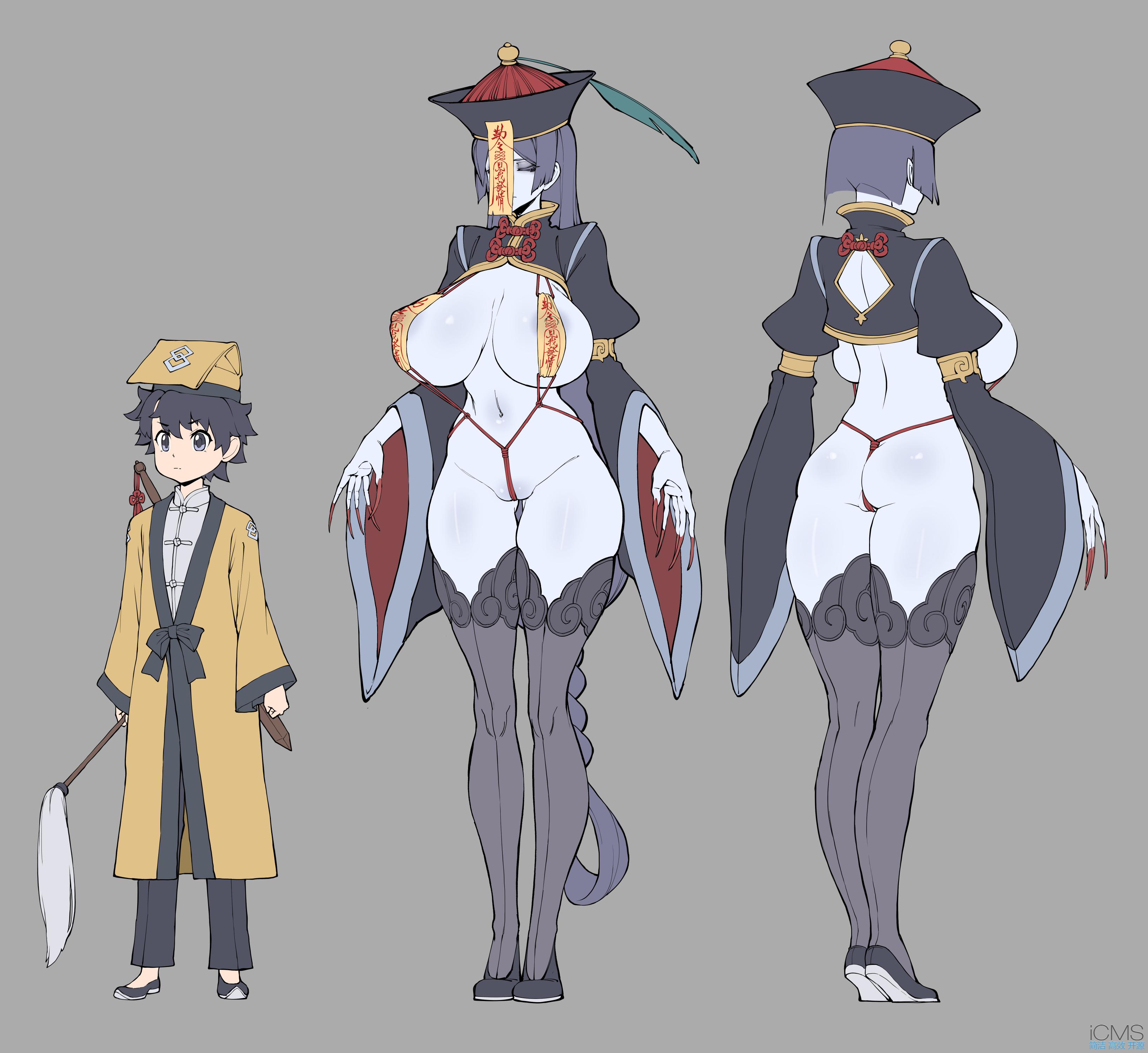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